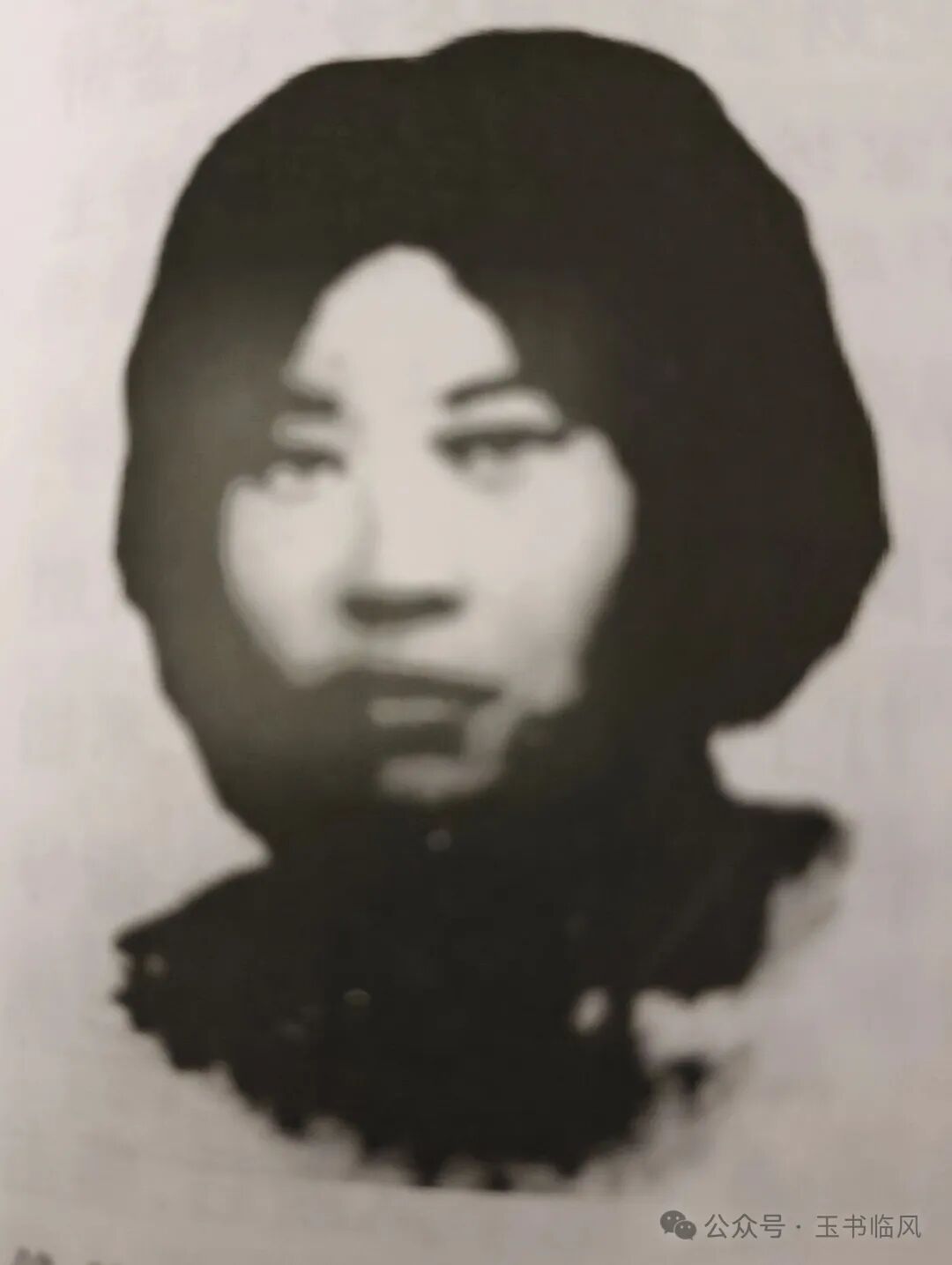
1912年8月,陕西省米脂县银州街道东大街小巷子的杜家宅院,一声清亮的啼哭骤然划破陕北米脂的宁静——这便是降生在商人家庭、日后令敌人咬牙切齿的杜焕卿。看着襁褓中这个眉眼澄澈的女婴,父母的心头漫过温柔的期盼,为她取名“明峰”,盼她能如黄土高原上的山峁般,稳稳立世,一生平顺无虞。谁也未曾想过,二十二载春秋流转后,这个自幼在锦衣玉食中长大的姑娘,会以“鸣凤”为化名,在南京宪兵司令部阴森的囚牢里,用生命发出震撼人心的最后啼鸣。
米脂女子高等小学的课堂上,当先生讲到“妇女解放”四个字时,杜明峰的眼里瞬间亮起灼人的光——那时的她还不知道,这四个字将化作她短暂一生里熊熊燃烧的火把,照亮前路,也燃尽自己。
彼时的陕北,多数女子的脚上还缠着长长的裹脚布,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古训像一道沉重的门闩,死死锁着深宅大院里那些黯淡的光阴。可杜明峰偏要撞开这扇腐朽的门。三民二中的校园里,她和尤祥斋、张惠敏等一群进步女生,常常聚在老槐树下,把《新青年》上那些振聋发聩的文章抄在粗糙的麻纸上,趁着沉沉夜色,将它们贴满城墙的每一个角落;庙会戏台旁,她挥毫写下“男女平等”的标语,字迹工整得如刀刻一般,转身又换上演出服,伴着《国际歌》的旋律翩然起舞,裙摆扫过围观者满是惊异的目光,将新思想的种子悄悄播撒。
母亲曾摔过她藏在箱底的进步刊物,父亲红着眼怒斥她“辱没门楣”,巷口的三姑六婆见了她,总会啐一口“疯丫头”。可这些,她听过就忘,像抖落衣角沾染的沙尘般毫不在意——心里的火苗正旺,哪顾得上这些冷言冷语的吹拂。1929年,她攥着入团申请书的手微微发抖,宣完誓的那一刻,悄悄把“杜明峰”三个字藏进心底。从此,她是“鸣凤”,要为心中的信仰啼出血来。不久后,她举起右拳,成为一名共产党员,拳头攥得那样紧,仿佛握住了整个民族的未来。
1931年的秋夜,陕北特委的油灯下,同志们急得直搓手——派往平津汇报的代表,还缺一大笔路费。杜焕卿(此时已常用此名)揣着心事摸黑回家,从家里取走一百块银元,借着窗棂透进的清冷月光裹紧布包,指尖触到银元冰凉的花纹时,心口却烧得滚烫,那是为信仰奉献的热忱。
再后来,她的学费、衣物、首饰,一件件陆续消失了踪影。换来的钱,化作了党组织的活动经费、同志们的药费、进步刊物的印刷费——最终都成了滋养革命的养分。
1932年风声日紧,榆林女子师范的课桌前,课本还摊着未合的页角,反动军队的刺刀已逼近校门,寒光刺目。全城张贴的通缉令上,她的名字赫然在列。9月,她乔装打扮,换上打补丁的粗布男装,混在拥挤的逃难人群里,辗转来到北平,中华中学的课堂成了她新的战场。
同年冬与赴北平汇报工作的陕北特委联络员毕维周——那个同样为革命奔波的青年,结为革命伴侣。他们在北平租住的小屋,墙上的《北平地图》看似寻常,其实街巷交汇处的红圈都是接头点;枕头下的油纸包里藏着情报,字是用米汤写的,要蘸着碘酒才会显影。有时毕维周半夜回来,她会端出温在灶上的小米粥,两人就着昏黄的油灯,把这个“家”过成了最隐秘也最坚固的战场。
1933年5月的清晨,天刚蒙蒙亮,“哐当”一声巨响,门板被枪托撞得粉碎。叛徒缩在宪兵身后指认时,杜焕卿正和战友交换情报。她几乎是凭着本能,左手飞快地将情报揉成纸团塞进嘴里,右手同时往窗边推了战友一把,眼神里的急切像火星般迸射——后窗下有棵老槐树,能藏人。
宪兵队的刑房里,烙铁烧得通红,竹签浸在刺骨的盐水里。当竹签刺进乳头的刹那,她疼得浑身弓成虾米,冷汗浸透了囚衣,却死死咬着嘴唇,血珠从嘴角渗出来,硬是没哼一声。敌人以为年轻女子的骨头软,可他们不懂,米脂的姑娘,骨头里掺着黄土高原的砂,碾不碎,砸不烂,有着钢铁般的坚韧。
从北平宪兵三团到南京宪兵司令部一号牢房,铁镣磨破了她的脚踝,留下一圈深褐色的疤。她在墙上用指甲划“共产党员”四个字,划了又划,直到指尖渗血,字痕深深嵌进砖缝里,像给这冰冷的墙,刻上了滚烫的印记,那是信仰的温度。
她身怀六甲在狱中艰难生下婴孩,谁知孩子夭折竟引发中风,病情垂危。敌人想借丧子摧垮她,狞笑逼问“招不招”?她抚着空怀落泪,抬头时声音嘶哑却如钢铁:“不知道。”最终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。
1934年的南京,冬天来得格外早。冷雨敲打着牢房的铁窗,发出沉闷的声响。22岁的杜焕卿躺在草堆上,呼吸渐渐微弱。她终究没能等到陕北的红旗漫卷黄土高坡,没能看到自己写在传单上的“解放”二字,如种子般在大地间生根、发芽、生长。
如今,南京雨花台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,她用过的毛笔静静陈列,笔锋间仿佛仍凝着当年抄传单时的千钧力道;米脂县博物馆的“妇女史展”上,她的事迹被一遍遍讲述,听者眼中总泛起潮意。那个曾被斥为“疯魔”的姑娘,早已化作米脂山上的风、黄土高原上的光——风过处,是她未竟的《国际歌》余韵;光落处,是她用生命守护的、如今繁花似锦的人间。
鸣凤虽逝,啼声不朽。